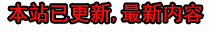|
近年来,在城市交通治理方面,北京大胆尝试了一系列政策实验,比如提高停车费、私车额度摇号、尾号限行等。为保障世界田径锦标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顺利进行,从8月20日至9月3日北京开始实施单双号限行。 北京是国内第一个通过采取尾号限行来治理交通拥堵的城市,首次限行是在2007年北京奥运测试赛期间。由于北京的示范效应,尾号限行被一些城市采纳,尤其是在城市举办重大活动期间。相比其他尾号限行方式,单双号限行只允许一半的机动车上路通行,达到了行政手段干预公众出行的极限,恐怕今后一段时间内国内不会有比它更苛严的“禁行令”了。 如何破解一个2000万人口的城市交通治理难题,世界上可以参照的经验本来就少,即使是他国的成功经验,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差异巨大,政策移植“成活率”究竟有多高,尚有待“试错”或“试验”之后加以评价。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成功与否、效果如何,北京的这些创新做法,无疑为中国的高密度城市,乃至世界城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那么,单双号限行实施之后,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呢?从北京市交通委通报的路况来看,路网交通压力明显缓解,处于基本畅通级别,达到了预期的缓堵效果。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地面公交相比同期提速约6%,主要通道早高峰平均运送速度约为35公里/小时。 可以看出,单双号限行使路网总体有所改善,但公交分到的“红利”相对甚少。虽然管理部门积极采取了增供措施,如公交提高2%运力、地铁早高峰延长运营时间30分钟等,但面对之前早已饱和的公交和地铁客流,公交系统如何快速、平稳地消化限行所产生的转移客流,确实是一个不小的现实挑战,也是其他已经采取或打算采取限行方式的城市不得不面对的管理难题。 不妨简单分析一下限行之后“谁受益,谁受损”。我们会清晰地看到,如果政策重心仅仅在于限行,而不是真正把路权还给公共交通,那么限行也只是单双号开车者的“公平游戏”而已,无法实现缓解交通拥堵、提升社会福利等最终政策目标。 考虑交通系统中有“开车者”和“公交乘客”两个类别,单双号限行将开车者划分为“允许开车”和“限制开车”两种状态。限行措施迫使一部分原先开车的出行者采用其他方式,从而减少道路上的通行车辆数目,达到缓解拥堵的目的。 首先,对于允许上路的车,由于上路的车辆减半,道路畅通,车速提升,出行时间有所节约,驾车费用略微下降,他们显然是受益的群体。 其次,对于被限制开车的人,或改乘公交,或改用其他方式(自行车、步行等),出行时间相对延长,公交的费用相比开车有所下降。受益与否取决于他们的时间价值和具体的出行费用,如果出行时间延长所导致的成本小于出行费用的节约,那么将有所受益。 第三,对于原来的公交乘客,如果没有大幅增加公交车数量和发车频次,公交车将更加拥挤,并且乘客有挤不上车的风险,虽然限行之后公交车速略微提高,行程时间稍降,但总的出行时间可能延长。 进一步,限行规则使前两类开车者的权利在单双日进行轮换,无论损益,都维持了开车者之间的公平性。就是说,相对于限行之前,开车者的出行效用确实有所下降,但由于存在单双日的轮换,不论处于“允许开车”还是“限制开车”状态,开车者之间相对都是公平的。 而由于公交供给涉及的因素相当多,原来的公交乘客极有可能成为“受损者”:限行所产生的转移客流,将与他们一起争夺原本就稀缺的公交资源,并产生新的拥挤和行程的不确定性。因此,限行的最大受损群体只可能是原来的公交乘客。 在限行之后,尽可能地调整地面公交的路权(增设专用道、延长公交通行的绿灯时间等),增加公交和地铁的发车频次,让公交走得比私车更快,让公交地铁运行更准点,才有望保证原来公交乘客的损失不扩大,从而实现政策执行过程中多个利益主体的共赢。 按照北京市交通研究中心发布的《2013年北京交通发展年报》,2012年公共汽(电)车出行量为826万人次/日,轨道交通出行量为509万人次/日,小汽车出行量为990万人次/日。公交、轨道出行量总和约是小汽车出行量的1.35倍,而公交、轨道出行产生的拥堵、污染等外部效应远低于小汽车出行,在政策设计中应优先考虑哪一类出行者的利益,不言而喻。 尾号限行充分利用了行政手段的禁止、强制和惩罚的效力,对调整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缓解交通拥堵产生直接、快速的作用效果。但是,相对于拥挤收费,尾号限行缺乏让出行者自主选择的决策过程,损失了“付费分流”的弹性机制,因而更容易对替代方式(公交、地铁等)产生刚性的客流转移,将道路上的拥挤转化为公交地铁里的拥挤,并可能引发客流对冲、人群踩踏等公共安全风险事件,因此在实施之前需对政策的适用性、替代方式的承受力等关键问题,展开细致分析以及谨慎规划。 (中国牌照网编辑:KING) |